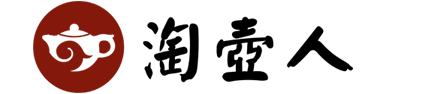曾有书册,所收之紫砂作品,是范曾先生与当今宜兴紫砂名工联袂所作。就书画而言,范先生于当今画坛固不作第二人想;以壶艺而论,则本册所载,皆当今之大作手,从制壶到刻工,均极一时之选,洵壶史之盛事也。盖紫砂自明万历间流布天下,数百年中杰出之名工,如时大彬、陈鸣远、杨彭年等间有特出,各领风骚;为之添一段文雅风流之文人韵士亦复不少,然王世贞、陈继儒坐而论道,指点壶师,并不直接参与创作;陈曼生从壶式到铭文皆有参与,是紫砂之大功臣,惜雅趣虽多饶,格局似嫌小;吴大瀓亦金石名家,能铭而不能画;以当世一流之书画大师兼诗人,而如此从事壶艺创造者,范先生是其人欤。此事于紫砂壶史,真可大书特书者。
以紫砂器为纸进行书画创作,于书艺画艺或不无微损,然奏之以刀,又别饶趣味;对于壶而言,则平添一段文风雅韵。因此书画家虽偶一为之,则有功于此道斯大。今雅好此道之藏家,往往独重器之工巧,此亦因世事之迁移,欲更求一文雅风流之陈曼生而难以得。故范先生此举,不惟是其书画生涯之一雅事,于紫砂事业之真正复兴功莫大焉。有鉴于此,本文不揣谫陋,列述历史上文人对紫砂艺术的贡献,以期辨明原始,阐发其意。
紫砂壶在中国陶瓷史和物质文化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以一器之微,不仅耗尽历代才人智士、名工巧匠的移山心力,更是价等黄金,珍同鼎鼐,耸动上至天子下至公卿士大夫,数百年啧啧人口者。
按工艺史上鬼斧神工之作在所多有,即以紫砂壶产生之日而言,如王士禛《池北偶谈》云:“近日一技之长,如雕竹则濮仲谦,螺甸则姜千里,嘉兴铜炉则张鸣岐,宜兴泥壶则时大彬,浮梁流霞盏则吴十九(号壶隐道人),江宁扇则伊莘野、仰侍川,装潢书画则庄希叔,皆知名海内。如陶南村所记朱碧山制银器之类。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欤?”上述的“一技之长”,尤其以紫砂壶显得“郁郁乎文哉”,好像特别地得到传统文人的赞赏。
那么紫砂壶的“必有可观”之“道”在何处?从工艺美术发展史的角度,论列历代名工的杰出贡献、探讨壶艺的设计制作史、详细品味壶艺的形、神、气诸方面的美学追求,都不失为研究的途径,且经学者和工艺名家的努力,这些方面的成果也很丰富。本文则着重探讨在紫砂壶史上的文人们,和他们的文化趣味,对这一特殊工艺作品的影响。
一、茶事与文事
宋皇佑二年(1050年)11月,蔡襄罢福建转运使,召还汴京修起居注,遂自福建经杭州,北上汴京。在离开杭州的时候,他给朋友友冯京(当世)留了一通手札:“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这通名为《思咏帖》的书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通过此札,我们能够想见当时文人雅士诗酒流连、佳茗美器相赠的韵事。
刚刚罢福建路转运使的蔡襄,是一位茶专家,转运使任上,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茶录》,这部茶学专著的问世,据蔡襄自己说,是因为“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因而向皇帝上书细论品茶之道的。《茶录》分上、下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之属。而蔡襄临行赠送冯京的礼物,就是茶和茶具。
所赠“青瓯”,之所以自谦“微粗”,按照《茶录》的观点:“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茶是中国文人的尤物。而茶具,自然也就成了书斋中的佳玩,不仅可以自用,也是馈赠的上品。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茶的描写,是晋杜育的《荈赋》,其中已经提到了茶具:“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陶之用以为茶具,其来尚矣。
关于饮茶的起源,众说不一。顾炎武的《日知录》卷七“荼”条:“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他在详细考证了《诗经》和《尔雅》中的“荼”乃是苦菜、茅莠之后,得此结论。此条也最为人常称引。唐陆羽《茶经》“六之饮”则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按“秦后始有茗饮”与“发乎神农”,本不相矛盾,但蜀人究竟何时开始饮茶,在秦并巴蜀之前,典籍无存,阙疑可也。
降自魏晋,则《三国志》中有以茶代酒之故事、《世说新语》有“水厄”之典故,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亦云:“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唐宋两代,是茶事大盛的时期。
唐代出现了茶史上的划时代人物——茶圣陆羽。《新唐书》陆羽传:“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 本传所谓经三篇,就是著名的《茶经》。陆羽著述颇多,《全唐文》载《陆文学自传》曾自述其历史地理等着,惜乎今已亡佚,惟《茶经》今日最著。
可以说,陆羽是第一个将饮茶这一人伦日用的事情人文化了的中国文人。《茶经》对当时的饮茶风气盛行,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茶经》“十之图”劝人将他的著作“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至此,饮茶已经不是一件和油盐酱醋等同的开门七件事,而是“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精致的文化活动了。
《唐国史补》载:“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陆羽的影响有如此之大。
《茶经》对于茶具有精细的论述,“四之器”记载了饮茶所用的24种器皿,并对其优劣进行了详细的评判,如“越州瓷、丘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这可以看作最早关于茶具选择的趣味标准论述。今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就是陆羽认为最好的越州瓷的最精者。
由于陆羽的提倡,茶开始“慕诗客、爱僧家”,逐渐地走入中国文学和艺术中来,从此在中国文人的书斋中,须臾不离。唐刘贞亮总结茶之“十德”,除了尝滋味、养身体、养生气、散闷气等食用功效外,还指出它可以有利礼仁、表敬意的社交功能,和可雅心、可行道的精神作用。唐朝的另一本茶书《茶述》云:“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则因其清、洁、和、静的特征,茶不仅是一款日常饮品,更是高洁心灵的象征和表达物。
和陆羽大约同时代的李白,写了较早的一首茶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山仙人掌茶》。序云:“余闻荆州玉泉寺……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侄位置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迭,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末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在李白看来,族侄所赠送的“仙人掌茶”,“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简直是神奇的不老之药。
而诗僧皎然,则写下众多的茶事诗,如《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陆羽上元初(760)在吴兴苕溪结庐隐居,遂与皎然结交,皎然在重阳节赋此诗,记赏菊、品茶的雅事。
酒在阮籍、刘伶、陶潜那里,登上了文学的舞台,现在,要面对一位清冷苦涩的竞争者了。范曾先生曾云酒“以水为形、以火为性”,平静的外表下是如火的性情,恰如中国士人炽热的内心,故嵇康借酒作穷途之哭、阮籍以酒避司马氏婚姻之约、陶渊明得酒便如羲皇上人、李白得酒则百篇珠玑;而茶,则以土为母、以木为形、以水为友、遇金而生、遇火而成,甘苦其味、清淡其性,平和中有丰富无限哲思,枯淡里蕴山泽云雾之气,它与酒恰成一文一武,代表了文人情怀的两极。皎然诗中打起的茶酒公案,恐怕是对美酒与佳茗同样酷爱的李白所不能首肯的。但皎然却是爱茶之情弥坚,《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不仅辩难不休,还要广邀同好,《顾渚行寄裴方舟》:“我有云泉邻渚山,山中茶事颇相关。……清泠真人待子元,贮此芳香思何极。”《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困寄元居士晟》:“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
白居易被贬谪江州司马,于元和十三年收到忠州刺史李景俭所寄新茶,作《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故园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这样赞美:“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茶诗》则广为人称道:“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从唐代开始,几乎每个时期的文坛巨匠,都对茶情有独钟,苏东坡有“佳茗似佳人”的慨叹、而作《叶嘉传》,黄庭坚有“不游轩石之华胥,则化庄周之蝴蝶”的快意,徐文长有“倾七碗,对三人,须臾梅影上冰轮”的良辰……这样的名单,我们可以开得很长,几乎等同于开列中国文化史上的所有著名的名字。
二、明代文人文化趣味与饮茶风尚的变迁
前文所述蔡襄赠送冯京的“大饼”,即宋代流行的团茶,团茶的制作工艺极其繁复,最精美者甚至值几十万钱。宋徽宗所作《大观茶录》,龙团凤饼,论述颇详,当时的斗茶风尚,也曾经风靡一时,惟本文不是论茶史,故阙而不述。
《明会典》:“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中发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茶芽以进,有司勿舆。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曰探春、先书、次春、紫笋。”这是茶史上一次重大的变化,从此,延续了几百年的团茶、饼茶风尚逐渐消退,团茶饼茶逐渐成为边贸互市的特有品种,散茶开始成为主流。相应地,饮茶器具也发生了变化。
洪武二十四年罢造龙团诏,不完全是朱元璋爱惜民力的举措导致的,自有其社会消费习惯的变迁。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著《茶谱》对唐宋团茶的品评是:“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茶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对“自然之性”的追求,对“真味”的新兴爱好,是饮茶方式转变的内在社会原因。散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但还不是饮用的主流,元代虽然一般社会大众开始普遍饮用散茶,但龙团仍旧是贡奉珍品,一般的认识,仍旧认为团茶的品格高于散茶。
宋徽宗《大观茶论》虽云“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间洁,韵高致静”,但观黄庭坚《煎茶赋》中,胡桃、松实、靡芜、水苏、甘菊之类,所加不厌其多,可知宋代之茶,颇像一碗粥,加姜既有“勾贼破家”之虞,和盐便得“速化汤饼”之效。
据茶史学者研究,宋朝时,散茶的名目只有日铸、双井和顾渚等几种,而黄一正在《事物绀珠》中所记明时著名散茶,已得九十多种。而且大多数是第一次出现的新茶名,在明代万历以前的一二百年间,散茶的品种大量的出现,表明它已经成为茶的主流。
因此,朱权的《茶谱》称“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在饮茶习尚的转变时刻,又是一位文人,对新时尚赋予了人文意义。
明代的文人是入世的。这种入世当然和儒家一贯倡导的不离人伦日用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明代的文学艺术整体呈现着一种“俗化”倾向,即如三言二拍之类小说的大量传布、文人热衷于写作传奇、书画家的商品化倾向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
但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有意味的现象,即入世的行为,往往用出世的方式来行事,最典型者莫过于所谓的山人。这种山人,既不隐居山林,又不高尚其事,而是凭借一两种技艺奔走于公卿之门,打秋风、夹篾片,清人蒋士铨笔下的陈继儒,可谓刻画入木三分:“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按蒋氏诗不免刻薄,虽然山人遭到整个社会的反感,甚至万历朝还出现了“恩诏逐山人”的政府驱赶行动,但也正说明,在科举制度的压迫下,出处无路的下层士人的焦虑心理状态。
上述陈继儒在年轻时即裂衣冠弃科名,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这种心态反映在对待日常生活中,便体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明代士人愿意沉浸在具体的一事一物的小趣味中,这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另一方面,他们则愿意将固有的文化趣味带入具体的事物中,为这些“什物”进行“雅化”的文化赋值。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浮华化,是以精致化的方式完成的。
如果说唐代的文人饮茶,其意趣尚不离禅家况味,宋人斗茶,已涉富贵气息,则明人之饮茶,却一定要强调茶品和人品的一致性:“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相得。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明陆树声《茶寮记》)我们可以在徐渭的传世作品行书《煎茶七类》中,明显地看到这种固执的坚持: “煎茶七类:一、人品。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领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辈、鱼虾麋鹿之俦。二、品泉。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并贵汲多,又贵旋汲,汲多水活,味倍清新,汲久贮陈,味减鲜冽。三、烹点。烹用活火,候汤眼鳞鳞起,沫浡鼓泛,投茗器中,初入汤少许,候汤茗相浃却复满注。顷间,云脚渐开,浮花浮面,味奏全功矣。盖古茶用碾屑团饼,味则易出,今叶茶是尚,骤则味亏,过熟则味昏底滞。四、尝茶。先涤漱,既乃徐啜,甘津潮舌,孤清自萦,设杂以他果,香、味俱夺。五、茶宜。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行呤,清谭把卷。六、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也。七、茶勋。除烦雪滞,涤醒破疾,谭渴书倦,此际策勋,不减凌烟。”
不仅茶,一切的日用什物,都不免被这种“雅化”的努力所覆盖,沈德潜《万历野获编》中所记载的当时人好尚,象新安墨、云南雕漆、刻竹扇等等,往往成为非常时髦的玩意,如竹扇:“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又如:“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
这种“时玩”(与古玩相对)“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 (《万历野获编》),起初不过因为某种物品“其精雅则宜士人”,继而成为波及整个社会的风气,巨商大贾纵横其间,更使得“时玩”身价增重。
所谓的雅趣、幽趣,其总的倾向是清润温雅、平和怡然,简洁精雅的入世方式,不离人伦日用的儒教原则,加之主流艺术风气的影响——当时主绘画坛坫的松江派首领董其昌,就是“平淡天真”风格的最大倡导者。我们不妨摘录董其昌的朋友、山人的代表陈继儒的一些言论,来看这种趣味的总体倾向:
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尘令人雅,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谈,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
文房供具,藉以快目适玩,铺叠如市,颇损雅趣,其点缀之法,罗罗清疏,方能得致。
吾斋之中,不尚虚礼,凡入此斋,均为知己。随分款留,忘形笑语,不言是非,不侈荣利,闲谈古今,静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适幽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陈继儒《小窗幽记》)
幽、远、爽、寂、清、冷、闲、简、旷等词汇,使最经常用来形容这种趣味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紫砂壶出现在工艺美术的历史舞台上。
三:文人立场:紫砂的诗意灵魂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云:“壶子茶具,用处一耳。而瑞草名泉性情攸寄、贵仙子之洞天福地、梵王之香海莲邦。”这个说法,与朱权《茶谱》中的观点几乎一致。既然茶之一事,既关乎人品清高,其境乃“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其侣亦“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轩冕之徒”,则其器自然不能苟简。
关于紫砂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也多所争论,归纳起来主要不外乎起于宋朝说、起于金沙寺僧说。前者依据于梅尧臣的一句诗,证据似嫌不足,后者根据传说,其来颇显玄妙。其实二者不妨调停一二。以紫砂泥成器,不妨时间稍早,甚至早于宋代也未可知,只是目前并无考古和文献依据。居此土而用此物,在古人不过就地取材而已,其事不必乌有,然而我们今天所谓的“紫砂壶”或“紫砂器”,乃是有特指的品种,不惟材质,不惟工艺,趣味才是关键。因此,供春其人既渺不可寻,传世所谓“供春壶”者亦不过聊供人神往,时大彬才是此道的开山作祖手,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注意到《阳羡名陶录》中的这段话:“时大彬号少山,……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瑘、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大壶小壶的问题,壶固然宜小不宜大,盖“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然而雅俗分野,殊不在此。陈继儒在紫砂产生的历史时刻对时大彬的关键性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了整个紫砂壶制造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回顾上述陈继儒在他的小品中的文字,可以说,直接就是壶的形神气的最佳描写——
“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岂非壶之制;
“令人幽,令人远,令人爽,令人寂,令人闲,令人侠,令人轻,令人雅,令人清,令人冷,令人韵,令人隽,令人旷,令人谈,令人野,令人怜,令人奇,令人博,令人古”,岂非壶之神与气。
可以说,在这一艺术奇葩诞生的那一刻起,名士与名工,便是密迩不可分的共同创造者。如果没有“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好事缙绅”的推波助澜,估计巨商大贾是没有兴趣在其中纵横捭阖的,既不能价重黄金,自然也就等同于一般商业产品或普通工艺品,不能够流布四方,即使天才如时大彬,也不过混同编氓,泯灭于历史而已。
检讨文人对紫砂历史的影响,大致有几个因素,上述文人趣味的取舍好尚是其一。
其二,则是文人固有的文化艺能,对紫砂制作的渗透。《阳羡茗壶系》:“规仿名壶曰临,比于书画家入门时。”直接将紫砂创作与书画创作相比附,是真有见地。盖紫砂的发展,与书画一道息息相关。董其昌云:“士人作画,常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对“士气”的追求,是松江派固守的艺术立场之一,这个立场深刻地影响了紫砂制作。《阳羡名陶录》序云:“上古器用陶匏,尚其质也。制度精而取法古。”以陶为器,在于“尚其质”,如同文人以水墨绘画。尚其质的美学追求,使得紫砂大师,不务妍巧,惟朴是尚。如徐友泉“诸名种种变异妙出心裁”, “然晚年恒自叹曰: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徐氏巧夺天工,大彬曾叹将来早就必超乎己,然而及至晚年,乃悟此道原不在精巧。再如:“时朋一作鹏,亦作朋。……与董、赵、元是为四名家并万历间人。乃供春之后劲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文巧”与“古拙”,在此处是壶艺高下之辨也,何尝不是书画的优劣之分。
对壶艺影响莫大者,是书画与壶艺的结合。如:“陈辰,字共之,工镌壶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家之中书君也。”
“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次则李仲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已。仲芳亦时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逊。”(周高起《阳羡茗壶系》)
吴骞《阳羡名陶录》:“余得一壶,底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制’,十字,皆行书,制浑朴而笔法绝类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后一名手也。”
对文字的特殊趣味,是中国文人的一大文化特征。不仅因此产生了书法这个独特的艺术种类,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茶壶款识能够书法娴雅,自然被高看一等。
再如陈维崧(其年)《赠高待读澹人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其上刻画蜼凫蹲,又如北宋没骨画,幅幅硬作麻皮皴。”壶艺之通于画艺,在行家里手看来,也是这样。
其三,是通过与文人的交游,历代名工不仅提升了自己的文化素养和艺术趣味,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声望,从而使得紫砂更加因人而重,声赫一时的名工巨匠,不仅受到各界的尊崇,上焉者自身也厕于士大夫之列。
在传统社会中,以技艺求生的工匠,往往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尤其是在器、道划分严密的士大夫那里。“时大彬,制砂壶名手也,尝挟其术以游公卿之门。其子后补诸生,或为四书文以献嘲,破题云:时子之入学以一贯得之。盖俗称壶为罐也。” (《阳羡名陶录》引《先进录》)连壶圣时大彬之子,都不免受到这样的侮辱,其他可知。因此,有人在交游士大夫后,不愿意言及自己的本业:“蒋伯荂……后客于吴,陈眉公为改其字之敷为荂。因附高流,讳言本业,然其所作坚致不俗也。”然而有见识的士大夫,对于不俗的人,还是有正确的评价的:“陈鸣远,其名尤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常至海盐馆张氏之涉园,桐乡则汪柯庭家,海宁则陈氏、曹氏、马氏,多有其手作。而与杨中允晚研交尤厚。”这些文人士大夫之所以与他交游,是因为觉得陈鸣远“此则鸣远吐属亦不俗,岂隠于壶者欤?” 这个评价甚至超出了对他本身壶艺的赞赏:“陈鸣远手制茶具雅玩,余所见不下数十种,如梅根笔架之类,亦不免纤巧。然余独赏其款字有晋唐风格。盖鸣远游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 ……” 不但如此,士大夫还乐于相互绍介:“我初不识生,阿髯尺素来相通(谓陈君其年也)。”(汪文柏(季青):《陶器行赠陈鸣远》)
其四,正因为名工社会地位的提高,才会有文人参与茗壶制作的可能。项不损是涉足此道的较早的文人:“项不损,名真,檇李人。襄毅公之裔也。以诸生贡入国子监。吴骞曰:不损故非陶人也。尝见吾友陈君仲鱼藏茗壶一,底有砚北斋三字,旁署项不损款。此殆文人偶尔寄兴所在。然壶制朴而雅,字法晋唐,虽时、李诸家何多让焉。” (《阳羡名陶录》)
而清代陈曼生,则成为了壶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曼生公余之暇,辨别砂质,创制新样、手绘十八式,倩杨彭年、邵二泉等制壶,为时大彬后绝技,以推壶艺中兴。曼生壶铭多为幕客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为之者。凡自刻铭、刀法遒逸,每经幕僚奏刀或代书者,悉署双款;寻常贻人之品,每壶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价三倍。” (《阳羡砂壶图考》)
郭若愚先生《漫谈陈曼生紫砂壶的造型设计》一文,整理搜集曼生壶的壶式及款识,认为“这是工艺美术设计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之事”。盖曼生壶的诞生,是紫砂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这一工艺美术品种在后来能够保持高度精致优雅特征的重要原因,当然是重要之事。
曼生壶的影响不仅是给后人留下了一批精心创制的壶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壶家与文人的合作模式,成为对后来紫砂艺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如金石名家吴大澂和黄玉麟的合作,也是紫砂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清末到民国,是紫砂发展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应该说,今天活跃在紫砂艺坛上的紫砂艺术家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艺术渊源追溯到这个时期。而此时的紫砂艺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开始逐渐摆脱单纯匠人的地位身份,本身的文化修养成为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任淦庭先生,本身即是由一定造诣的书画行家里手;顾景舟先生一生交游广阔,凡金石书画名家,都有很深的渊源。
由于特殊的机缘,民国时期一批紫砂艺人有机会大量学习观摩临仿前代经典作品,这些经验为紫砂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极其重要且特别的动力。因此,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著名紫砂艺人,像任淦庭、朱可心、裴石民、王寅春、顾景舟等,后来在解放后进入紫砂工艺厂传艺授徒,可以说是将文人壶的趣味、传统的经验和个人的艺术造诣等多项紫砂财富遗留给了后人。
四:对紫砂发展的省思
在紫砂产生的同时,一些其它工艺美术品种,如嘉定金陵之刻竹、端州之制砚、徽州之制墨,皆名满天下。砚墨固然其来尚矣,然而在嘉、隆、万之际,名手辈出,考其原始,文人的热情参与,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上述艺术种类,流风余绪,至今不衰。然紫砂壶于今特为显赫。不仅诸位工艺美术大师之名,昭昭在人口,阳羡诸名师,其一器之成,风行天下,即古之巨匠,亦不过如是而已。
古人一器,价重黄金,今人又远远超乎于此,是诚为紫砂事业之大幸。
然有识之士,在此之际,仍不免为紫砂之前途忧心。紫砂矿的枯竭,佳泥难得,即使名手,也要将有限的泥料珍若头脑眼目,是人人看得见的危机。然而却有一个深层的危机,或许还没有这样迫在眉睫,那就是在紫砂的制作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的“文人”的缺席。
这种缺席,有“名士”和“名工”双方面的原因。
先说“名士”。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便不复存在,知识精英逐渐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除了“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这一经典定义之外,更多的面貌是“术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士。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也不必全部都需要有以往文人士大夫的知识构架,则昔日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在逐渐的消逝之中,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应该说,在上世纪上半叶,一些仍旧保持旧日士大夫情怀的文人知识分子对壶艺的热情与参与,是紫砂壶艺于清末以后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顾景舟那一代大师的成就,与他们和这些人的合作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进一步说,自解放后紫砂工艺生产恢复以来,众多的书画家、艺术家也曾经广泛地参与到紫砂壶的制作中来,他们用自己的丹青笔墨,使壶艺有相得益彰的神采,他们也对紫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名工”的角度来说,今日之紫砂艺术家,较之过去的紫砂艺人,在眼界、素养、学识等方面,应该说占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印刷术倡明、博物馆事业发达,前人不能有如此方便的条件见识历代名作;即以本书中收录的诸位名手来说,很多人在专业的美术院校学习进修过,对于造型艺术的观念,与以往的人相比,自然有不同的理解。今日紫砂壶艺的出新,当然是寄托在这样的“名工”身上。
然而,这仍旧不能掩盖紫砂创作日益“工艺化”的现实。
首先,画家、书法家并不等于“文人”,绘画、书法作品加在茗壶上并不等于参与了“壶”的创作。今日欲求一有文人情怀的书画家,难矣哉;欲求一有古人情怀,且具有昔日名士学养者,更难矣哉;有此情怀、有此学养、有此手段,而有机缘且愿意为壶艺的发展做贡献,则可遇不可求。
其次,“工艺美术大师”决不仅仅是技术大师,更不仅仅是造型艺术师,“器”与“道”的微妙关系,就在一线之间,道也者,体乎此则为风雅韵致之艺术品,离乎此便为日常家用器物,最多不过富人架上炫耀之宝物。
所以,如何评价本书中的这些作品,就不仅仅是一个介绍鉴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为诸位作者赞美揄扬抑或品评长短的问题,用郭若愚的话说,“这是工艺美术设计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之事”。
所以我们先要辨明的是,这些作品决不仅仅是“茗壶加书画”的简单结合,而是紫砂发展史上,继陈继儒与时大彬、陈曼生与杨彭年之后的又一次“名士”与“名工”对这一工艺奇葩的历史性推进。
之所以作此论断,第一个理由是:今日欲求一铁线穿空、笔力抗鼎的杰出书画家,则范曾先生是其人;欲求一有古人情怀、且具有昔日名士学养者,则范曾先生是其人;倚此学养、倾此情怀、运此手段,而为紫砂壶艺做杰出贡献的机缘,则范曾先生于饮兰山房挥洒时也。
之所以作此论断,第二个理由是,本书收录作品,无论制壶、铭刻,均为当代一时无两之选。李昌鸿先生大师国手,得当代壶圣顾景舟真传而克绍箕裘;凌锡苟先生、倪顺生先生陶艺世家,渊源有自且能恪守传统不坠家风;毛国强先生刻陶圣手任淦庭之高弟,以陶为纸,纤毫毕现;蒋新安、桑黎兵、陈洪平先生今日陶艺之中坚;李伟、范顺君、吴勇后生可畏,可谓少长咸集。
之所以作次论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有浑无斧凿痕之鬼斧神工制作,必有天孙云锦之妙手补无缝之天衣,珠联而璧合,此器此形必为此书此画而设,此书此画必契此器此形之韵,然后镌以精工,互为彰显、互为发扬,方可称为合作。其画也凛凛乎风神,其铭也郁郁乎文哉,其制也茫茫乎若太古未凿,是则桑连理馆(陈曼生)中商量邃密、切磋琢磨之情境,重现于今日矣。
有是盛举,其陶艺将复大兴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