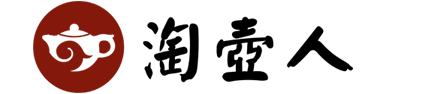您的一生是否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承继传统、积蓄文化、独立创新、开拓进取,一共四个阶段。
● 我不知道什么阶段不阶段的。只觉得在二十岁以前主要是在家乡跟父亲学习传统的紫砂制作工艺,正是由于父亲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之后就是到上海去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开阔了眼界,掌握了现代陶瓷的技术生产方法。再然后就回乡在家里的作坊做了一段时间,其间还当了一次义务的代理村长和夜校教员。到1955年时就到蜀山陶业合作社当起了社员。在朱老(朱可心先生)的鼓励下,工作之余,开始了自己的创新。十年动乱的时期,她们不许我碰紫砂泥,所以我憋着一股劲,平反后我努力工作,想挽回那逝去的十年时间,直到我后来做不动为止。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分阶段,但我的一生基本就是这么度过的。
○ 您认为这些经历中哪段经历对您最重要,是您艺术之路的转折点。
● 在上海的经历。
○ 我们通过资料了解到,您在年轻的时候曾两次去过上海。一次是受聘于上海铁画轩紫砂古玩店,和您伯父一起做仿古壶,另一次是受聘于上海虞家花园做花盆技师。是这两次经历吗?
● 是的。
○ 那您是什么时候进入上海标准陶瓷公司与顾景舟先生成为同事的呢?
● 进入上海标准陶瓷公司,是自己不想一辈子像伯父一样地做仿古壶,所以就找机会自己应聘到标准陶瓷公司。这大约是在第一次去上海时。好像是在1943年。
○ 为什么说这段经历重要?
● 那段时期的经历,特别是虞家花园的经历,为我以后的花货创作打了基础。要知道在那之前,我还是个乡下姑娘,我的作品虽然不俗,但脱不了一个土字。在上海让我开了眼界,这段日子对以后一直有影响。

○ 第一次去上海,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 上海的亭子间,就是那种很小的地方。
○ 那种生活空间是很小的,说明您当时生活的不容易。
● 我二十岁时,被上海铁画轩古玩陶器店老板戴国宝看中,他当年也是个陶刻名手,他把我带到上海和伯父蒋燕亭一起做紫砂器。初到上海,寄居在伯父家,十分不习惯。不到十平方米的地方居住着一家四五口人,通常不到十二点都没有我睡觉的地方。
○ 您当时对您的伯父了解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 我当时并不很了解,但是时间长了,就发现伯父几乎精通紫砂各个门类的所有绝活儿,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不是为生活所迫,他可以搞很多创作,留下许多传世精品。
○ 您是怎样看待伯父做仿古壶(指仿老)这件事情的?
● 我伯父一生从没有刻意要做什么仿古壶。因为我们制壶时,旁边没有任何供参照或借鉴的真壶,所谓的仿古壶,有许多都是伯父自己的壶样,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他才不得已把自己的壶打上古人的印章。
○ 没有古壶放在边上做参照,那你们是怎样做仿古壶的呢?
● 我们就是按照戴老板给的壶样或是按照客户们送来的图样,或者用伯父自己的壶样来仿制老壶。有些仿生的东西是就着实物做的,如伯父叫我做个小田螺,他就买个小田螺放在我的旁边,让我照着做。
○ 做好后再怎样处理?
● 这些东西做旧后分别由戴老板打上明清制壶高手时大彬、陈鸣远和陈曼生、杨彭年等人的印章,他有时是拿回去打印,有时就提着印过来打。打上这些名人印章的壶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仿制品,再以不菲的价格卖给那些附庸风雅的老板们。
○ 您现在还能认出您以前做的壶吗?
● 能,当时我们做壶时都自己留了记号,这种记号主要是做紫砂时的工艺手法留下的。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易看出。
○ 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来找您鉴定老壶。
● 是的,没想到四十年后,我自己做的一把仿古壶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 太有意思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 大约二十年前,香港商人罗桂祥来访时,错把我当年制的壶,当作陈鸣远的调砂《虚扁壶》,拿过来请我鉴定,最后,以壶易壶,我早年制的壶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 听说当年铁画轩曾聘请了一批紫砂名人做仿古壶,您在上海时是否见过他们中的一些?
● 当时听说裴石民和王寅春也在上海做壶,但我和伯父一直在自己的亭子间里工作,以前的老板是不会让我们见面的,所以没有见过他们。
○ 我们从资料上知道,您的伯父蒋宏高先生,又称燕亭先生,是个做紫砂的高手,光货、花货样样精通。
● 我父亲的手艺是跟我伯父学的,伯父没有正式拜师学艺,但他曾经跟一个雕塑高手学过一段时间。
○ 与伯父一起做壶时,他亲自教过您吗?
● 没有正式教过,主要就是让我在他身边看。他做《莲蓬壶》时,我在他身边,看完了我就会做了。在他身边习艺,其实就是他在教我。
○ 《莲蓬壶》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 先在做好的泥坯上,用这样的小刀在上面这样一转,挖出一个洞来,里面的洞一定要很大而且圆。然后把做好的莲子放在里面。再用竹尖刀在洞口处按捺收平,使莲子不易掉出即可。
○ 伯父对您现在走的紫砂之路是否有什么影响?
● 伯父是让我看到了一个旧社会紫砂艺人的悲哀,他的一生没有自己的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作品,手艺虽然好,却不能使家人过上小康的生活。生命终结时只能带着无限的悲叹离开人世。他还让我明白了在上海铁画轩干活,不是我要走得路。所以我找了个机会应聘到了上海标准陶瓷公司。
○ 您在上海标准陶瓷公司主要是做什么工作?
● 我主要是做工艺辅导员,告诉大家怎样做才能把东西做好。
○ 这时期的工作对您以后在紫砂工艺厂进行工艺创新很有帮助吧?
● 是的,在上海标准陶瓷公司,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许多制作陶瓷器的规范化的方法和程序。另外,上下班的路上还可以看到上海这个令人心动的花花世界,所以这是段很有益处的经历,而且这里的工资还比较高,三十元一个月,在当时已经不少了。
○ 那您为什么要离开标准陶瓷公司?
● 那是1943年,因为标准陶瓷公司的老板贩卖日货,投靠汪伪政权。虽然公司没有倒,但是我和其他有骨气的人都决定要离开那家公司,恰好当时伯父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在此期间,我一直是寄住在伯父家的,因此我们一起回到了宜兴老家。就这样第一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就结束了。

○ 您在乡下这么闭塞的地方,是怎么知道上海望族虞家需要一个紫砂花盆技师的呢?
● 我是没法知道的,回乡后,我们在县城找了个门面开了家“宏生紫砂店”,在店里卖些自家的产品。由于我的手艺招徕了不少远道的客人,于是我认识了范敬堂老先生。范老先生很爱我的紫砂才艺。由于他的介绍,使当时家境窘迫的我重回上海,1944年在虞家花园里做起了花盆技师。
○ 您曾说过虞家花园的经历对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您还记得虞家花园在哪,记得它是什么样子吗?
● 让我想想:虞家花园好象是在协庆路上,具体几号已经记不清了。它是一座拥有几十个房间的三层法式园林建筑。据说,这套府宅只是虞家的一部分。
○ 它的主人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还记得吗?
● 主人好像叫虞顺恩。听说他早年一直在四川做官。我在虞家花园时只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先生,言语不多,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博古通今无所不晓,让我第一次在生人面前感到缺乏底气。说到紫砂,虞老先生更是如数家珍,好多事情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我想,即便是伯父,恐怕也没有他那么通晓。但虞老爷露过一次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听说他生病住院,本来想在走时,再跟他道个别,但管家说不用了,所以也就没去。
○ 虞家花园有什么魔力,让您认为这段经历是艺术之路的转折点?
● 虞家花园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说起来真的不少!
○ 您慢慢说。
● 我在虞家花园主要管设计紫砂花盆式样,我下面有六个成型工人协助我制盆。由于花园中的植物品种众多,所以让我熟悉了各种花盆造型,它最小的只有酒盅大小,最大的可容纳百年古松。从成型工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制盆的成型技术。另外,在配色上,什么样的花配什么样的盆是很讲究的,有时主家还会要求在花盆上刻点东西,这又锻炼了我的陶刻功夫。在这儿,我在紫砂陶艺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锻炼。制盆和制壶道理相通,这为我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 在虞家花园的经历中有没有特别让您难忘的事情。
● 有的,我最难忘的是有一天傍晚,管家来找我,说老爷高兴,是因为特别欣赏我设计的两款造型花盆,一件是花口喇叭盆,一件是铺砂六方小盆。管家又说老爷吩咐让打开专放古玩字画的珍宝斋,让我开开眼界。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的书画、玉器、漆器、铜器等,简直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只能央求他们让我慢慢看,他们破例同意了。我一个人在一间别人不知道的屋子里慢慢看着,当时那种被打动的心情没办法说,过后许久,我才明白,原来紫砂的许多造型都是从毗邻艺术中借过来的,和那些精妙绝伦的东西相比,紫砂还远未成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是否可以这样说,虞家花园的经历彻底开阔了您的眼界,提高了您的气度。这是否也是您日后做花货“花而不俗”的原因?
● 也许是吧。但好景不长,九个月后,我带着些惆怅,离开了正在败亡的虞家,又重新回到了乡下。这些人和家族的命运彻底断绝了我对花花世界的向往。从此,我结束了看世界的日子,安安静静地开始做壶。人就是这么奇怪,在那里虽然只呆了短短九个月的时间,但在那儿所接触和接受的一切对我以后长长的一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您的一生中还有没有其它人或经历对您的紫砂创作起过作用。
● 说不上来,但我的记忆中总有几个挥不去的影子。学校里教书的林先生、丁蜀镇的开明绅士华荫堂先生、二洞山人储南强先生,他们都一直鼓励我从事紫砂创作,没有他们我可能也走不到今天。对于林先生,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把自己的第一把壶《木瓜壶》送给他时,他给我写的一段赠言:“凤之壶艺,若蚌之藏珠,自生自成;开壳之瞬间,即光照遐迩。珠玉之养,若胎儿之于母体,无须外力推动。玉汝于成,大器在望矣!储南强先生也是鼓励我从事紫砂创作的人之一。但最重要的一位却不是他们,而是朱可心朱先生。
○ 说说您记忆中的朱可心先生?
● 朱先生于我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假如先生还在世,应该是个一百零二岁的老寿星了,可惜老先生已于1986年走了。他对我就像父亲般的疼爱,他是在全中国挣工分搞机械化生产时支持我搞创新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帮助我前进的人。
○ 怎么说?
● 在我创作《牡丹壶》的日日夜夜里,朱可心先生一直给我以父爱般的关怀。先生毕生最擅长的是花器和筋纹器。因此,在泥料的配制、造型的比例等技术问题上,给我提出了很多让我豁然开朗的意见。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做《牡丹蝴蝶壶》时,朱先生正好从我身边走过,我把自己做好的壶给他看,他看了笑笑说,这壶把做得不太好,牡丹的枝应是从树芽中抽出来的,才能表现它的生命力,说着他就示范给我看。我觉得他说得对,就改了。

○ 他对您提供了直接的指导。
● 先生对我的好还表现在这壶进窑后,他还放心不下,三番二次到窑上去转悠,一会儿从火眼里看看火,一会儿叮嘱窑工几句。直到壶顺利出窑了,他才露出我少见的笑容。他对我的帮助和关怀还远不止这些。
○ 还有?
● 先生和师母都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有空,我经常去他们家串门,先生总是让我看他珍藏的老茶壶,给我讲紫砂前辈的故事,有时也谈谈技术革新的事。师母知道我喜欢吃面食,就经常给我包馄饨、擀面条。有一次朱师母说,蒋蓉啊,可心和我这么喜欢你,你就做我们的干女儿吧。事实上我并没有叫过他们一声干爹干妈,但我确实把他们当成自己的长辈一样来敬重。但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却给朱先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由于朱老在各种场合推崇我,结果紫砂工艺厂竟然有人贴了一张漫画,攻击朱先生和我。画面上涂脂抹粉的我正在做壶,朱老龇着牙,一脸坏笑地站在我旁边,他的身后竟拖着一条狐狸尾巴,漫画的作者唯恐读者看不懂,还加了一行注解:名曰技术创新,无非利欲熏心。
结果这张画把经历了一生坎坷,把名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的朱老气得够呛。第一反应是差点晕倒,最后被几个徒弟搀扶着送回家中。我当时表现还好,很冷静,因为我相信自己。直到镇委书记亲自来紫砂厂宣布那张漫画是带有污辱性的“毒草”,应予追查严处的那一天,我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