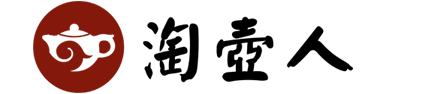石瓢壶是清代后期曼生壶中的一种式样,壶身为圆台形,盖为平顶式,桥式纽,直流、壶柄为牛舌式,壶壁上宜书宜画,因造型古雅,又便于刻绘装饰,遂成为紫砂壶的经典器形。但后来所制的石瓢壶,器形并不整齐划一,也是在形体轮廓大体相似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
石瓢壶是紫砂传统经典造型。溯源历史,有相关资料和实物佐证,当在清代乾、嘉年间。历代名家制作较多,但每人风格各异,其品种主要有高石瓢、矮石瓢、子冶石瓢,本人都曾制作过。并在此形上创作开片石瓢,均受人喜爱。但我认为还是以高石瓢为优。试以高石瓢为例谈谈其造型特点。
高石瓢造型简练,古朴大方,端庄稳重,刚中有劲,敦实调和。壶的体形是以两条抛物线结合而成,一条是从口到底的转角处,一条是底中心至底的转角处。两条抛物线略有不同,但要运用得当,结合得恰到好处,感觉刚中有柔,和顺有劲。盖虽是平盖,但实质上中高周低,中间和边沿有一毫米的差距;盖板线厚薄正好,线要圆、润,下边要与口结合严密,上边与盖面的交接要和顺而;又要突出盖板线的圆整有劲。 盖上的桥梁的(钮)是最关键之处,高矮跨度都要有符合比例的形,变化较大。要抓住每一个细部:桥中央是最狭处,慢慢向两面延伸至盖,特别是与盖的结合处要形成椭圆形,但又不是整个的,而是个三分之二椭圆;桥与盖的交接处要似明似暗,看得清但不明显;其内孔与盖的结合处缓转匀称,内孔也是三分之二个椭圆,与桥形成呼应;桥的两侧对称,处理手法难度较大,需耐心才能达成。
壶嘴称为直筒暗嘴。首先注意长短、粗细的比例恰当,自然,不能相差丝毫。从嘴头至壶身,逐渐加粗,就像是从壶体上生出来的感觉。至嘴端1厘米左右是直形,但看起来有些喇叭形,这是视力的错觉。嘴的角度恰到好处,面要平整,内孔要圆,嘴内径是出水口最小越往里越大,这样出水冲力有劲,不易涎水。
壶把要与嘴对称,把内外都是和顺流利的三角形线条,把头与壶体结合与嘴相同,自然流畅。(把手的横断面外圆内平似圆头三角形)把握使用舒适。 壶底部三足称围棋足,形如围棋子。足与底面结合清晰利落,三足位置呈等边三角形,要求匀称不偏,使整体统一,显示出一把壶的神韵齐全,风度大气,实用大方。
石瓢在我们行家来说是永远跌不破的形(还有掇球、仿鼓、掇只等)。意思是说这些形很受行家喜欢,虽历经几百年还是推崇倍致,并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壶中百变,首推石瓢。
石瓢壶身,源自舂米的石碓,口小腹大;但不同于石碓掘地半埋,石瓢壶以三足立身;旧时为避尘秽,农家借用锅盖遮挡,故此锅盖拎手演进为石瓢独有之过梁。其身碓形、底置三足、其盖桥钮,此三要素构成了石瓢遗传的DNA基因。作为个人臆断,虽有些异想天开,但求证过程颇是小心谨慎,既见生产实物,又有生活体验。博学的高振宇就创作过一只碓身石瓢,算是例证吧。
石瓢起源之另一说,应自顾景舟引用古文“弱水三千,仅饮一瓢”,而将“石铫”改称为“石瓢”,从此相沿均称石瓢壶。据清末旗人震钧《茶说》谈到“器之要者”,当属铫。作为吊在炭火之上的烹煮用具,“铫以薄为贵,所以速其沸也,石铫必不能薄;今人用铜铫,腥涩难耐,盖铫以洁为主,所以全其味也,铜铫必不能洁;瓷铫又不禁火;而砂铫尚焉”。所以,紫砂铫取石铫形意而成壶,但已不具烹煮之功,仅作沏泡专用。陈曼生与朱石梅分别在其参与的石铫壶铭文: “煮白石,青灰透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梅花一瓢,东阁招邀”, 想来这也是顾老为之更名的直接依据。
石瓢制作大家以清中期杨彭年为上。他所制石瓢有高、中、矮之分;有圈把、提梁之别。并与陈鸿寿合作弧曲面的“曼生石瓢”,朴茂祥和;与瞿应绍合作直坡面的“子冶石瓢”,刚劲明快;与朱坚合作虚盖的“石梅石瓢”,浑厚高古。更为经典的是文人雅士有感而发,将诗书画印集于壶身,切水、切茶、切壶型、切感怀。 “不肥而坚,是以永年”、“爱竹总如教弟子,数番剪削又扶持”等等,充满了人生的况味。
顾景舟制作、吴湖帆与江寒汀书画的合作壶,是当代石瓢壶的扛鼎之作。曾创出紫砂史上的神话:拍卖价折合人民币为100多万元。不以金钱的杠杆衡量,只以艺术的角度评价此壶,它当之无愧的。石瓢壶虽是仿古之作,但顾景舟大师不因袭传统,将毕生的修为了然于胸,机杼独运。景舟石瓢强化浑圆之身,蓬勃沉雄。压低拱形桥钮,待势而发。“有神斯秀,有气乃润”,作到了神完气足。因此极具现代审美。
石瓢壶久盛不衰,还在于壶型优势。自编顺口溜为:“下大上小梯形身,利于聚热和发茶;压盖阔口桥形钮,方便提拎清茶渣;三足鼎立壶身扁,安稳摆置好端拿;壶面宽广宜书画,喝茶品壶才为雅。”
我最喜欢的壶型是子冶石瓢。它的整个壶体巧妙地运用了三角形的对照变化,身筒与盖合为一个大的三角,把圈为三角,钮为三角,三足也构成三角,甚至直流与身筒也构成了“虚”的三角。这些三角更能巧妙而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子冶石瓢是几何壶型中运用三角形的经典之作。不过,器形的流畅与和谐还不是我喜欢它的根本原因。在把玩欣赏好的子冶石瓢作品时,我常常感到壶体中透出一种“骨力”,简洁利索、清奇脱俗。壶身内外氤氲着一种刚健挺拔的风骨,一种正直文人所特有的不同流俗、遗世独立的风骨。有时,我甚至偏执地认为子冶石瓢上只有刻绘一二或纵或横的竹枝最为合适,最有逸趣,因为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地具备“风骨”。因而用子冶石瓢泡茶,我常常感觉是在和一位高士对饮交流。
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的审美趋向呢?或者说,在我看来为什么子冶石瓢的造型能带给我这样一种充满骨力的“感觉”呢?
我想到了审美心理上的一个重要概念——移情作用。美学家朱光潜说: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这样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多的,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些诗句中的观者无疑和外物已难分解,似乎有“庄周梦蝶”的趣味。我想我与子冶石瓢的对饮或许有这么点意思。但有一个问题随即产生,就紫砂壶而言,为什么此型能使人产生此情而彼型则会使人产生彼情呢?若敬亭山乃荒山一座,李白还能看不厌吗?鸟儿的鸣叫若轻柔婉转何来“惊心”?由此我想,我们欣赏不同风貌的紫砂壶而产生的不同审美心理从主观上讲是移情作用的结果,而客观上紫砂壶本身的造型则给了我们“移情”的基础。
回到子冶石瓢这个“客体”,它是怎样给人“骨力”之感的呢?我觉得关键就是内在的整体骨架要清晰。因为骨是生命和行动的支持点,表现出内部的坚固支撑力,给人坚定的力量。“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画者没能很好地通过骨架来表现虎的力量和气魄吧。联想到紫砂壶。如果内在的结构缺少力度,甚至模糊不清,整体必不能产生充满“风骨”的感觉。
当然只有“骨”而没有“肉”,就会给人一种干涩枯瘦的印象,若只有“肉”而没有“骨”又会显出臃肿无力的样子,当然也没有丝毫美感可言。经常看到有些所谓创新的壶形,流、把甚至身筒都无原则地加粗,简直“胖”得没道理!或许作者有其独到想法,但这样的壶形实在让我经常联想到日本的相扑运动员。对于骨肉的关系,我们还可以拿中国书画来比较分析。书画中的骨力并非是剑拔弩张、横眉冷对,而是在笔墨间凝聚了一种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艺术家的内心。比如书法上有“点如坠石”之说,其实这“点”并非只是一个墨点,它的内部会发挥出一种力量。再如中国画的竹子,虽不讲究透视却也有充分的立体感,我们会感到一种骨力、骨气。同样,有骨力的紫砂壶给人的感觉是不仅“站得稳”,更有挺拔昂扬、精神抖擞的样子。“肉”是附着于“骨”之上的,“肉”要多少才恰到好处,那要看整体是否和谐、匀称、有力。就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由于他熟悉人体骨骼,因此他的人体雕塑透着一种内在的美。而他又擅长表现人体带有刚性富有质感的肌肉,所以他的作品英气逼人,骨肉匀称,栩栩如生。在紫砂壶的众多造型中,我觉得筋纹器最能考验工艺师在骨肉关系处理上的能力。好的筋纹器既通过清晰的线条与方圆很好地使壶体挺拔有力,同时也拥有温润饱满的“血肉”。比如时大彬的菱花壶,欧正春的菊瓣壶,汪宝根的仿古葵壶,还有一些成功的如意仿古都能达到骨骼有力,血肉丰满的境界。
紫砂界的朋友经常喜欢用“骨肉亭匀”来形容一把壶既有内在风骨结构又有均匀丰厚的外部造型,我觉得这个词很好地诠释了紫砂壶造型中骨与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