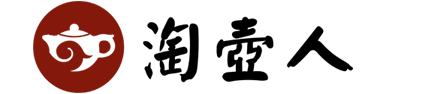“铫”(diao四声)亦称石铫、纱铫,即煮水的容器,在古代茶书中又称“水釜”、瓢、鼎、镬。辞海中的解释为:“吊子,一种有柄有流的烹器。”辞源中的解释为“有柄有流的小型烧器。”
根据《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军著)中先容,受中国明清烹茶道影响的日本煎茶道中使用的纱铫,一般是用白泥或红泥制成,容量在500—1000毫升之间,其中以日本文政时期(1818—1830)从中国潮汕、漳州地区入口的“文政渡砂铫”闻名。“文政渡砂铫”以白泥为料,壁薄如纸,煮出的水口感柔和,用此水泡出的茶香高味道美。而日本煎茶道则是在17—19世纪间将中国明代的文士茶变通定格,汲取营养,咀嚼其精髓而创成的。
从目前所知的中国历代茶书的内容中可以考证:在明代之前作为煮水的容器“铫”并不太讲究,只是“铜锺鼎鋞鋗鉇铫”中的一种铜制容器,而一般茶人只是较注重候汤的重要性。直到明代文士茶的流行与普及,对于茶器的讲究又上了一个层次。在明代张源《茶录》(1595年)中提到“桑苎翁煮茶用银瓢,谓过于奢靡。后用瓷器又不能持久,卒归于银……在山斋茅舍,惟用锡瓢,亦无损香、色、味。”而在中国茶史上据有重要地位的明代许次纾的《茶疏》(1597年)中有了更深的解释:“煮水器: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铫必穿其心,令透火气,沸速则鲜嫩风逸,沸迟则老熟昏钝,兼有汤气……”文中第一次提到“穿其心”的铫,也是历代茶书中提到“瓯注”时,以为“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往时龚春茶壶,本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其余细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质恶制劣,尤有土气,绝能败味,勿用勿用。”其后的茶书如屠本畯《茗笈》(1610年左右)中也有引用。而在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然炉头风雨声,铜瓶易作,不免汤腥,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以制差铫,能益水德,沸亦声清,……”从此以后茶铫都以锡制为佳。从上述的茶书资料可以知道,穿心铫与时大彬的茶壶在明代万历年曾流行成时尚,且1597年左右时大彬的壶以粗砂为主,而跟着时间的消逝及泡茶方式的改变,穿心铫的名称也为人们徐徐淡忘。
穿心铫是明代紫砂茶具发展方向之一。但明代紫砂茶具的发展过程却颇多疑问。作为创始之器的供春壶始终无法确认。按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紫砂壶创始于金沙寺僧,后传于供春,供春擅作小壶,后时大彬游娄东后学作小壶。然后名工辈出,不可胜数。金沙寺址尚存,然又有明末周容《宜兴壶记》云:“始万历间大潮山寺僧。”大潮山在宜兴与浙江长兴交界处,寺址不可考。所谓寺僧当为后人托古之辞,不可信。“供春”首见于万历二十五年许次纾《茶疏》,原文“龚春”;万历三十二年闻龙《茶笺》亦记有“龚春”壶。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证为“供春”。吴骞引申为颐山家童。《宜兴县志》:“吴颐山,仕,正德丁卯发解元。”看来即便(龚)供春其人无误其作品也无法确认。所谓供春小壶亦无从说起。
金沙古井出土的紫砂提梁壶与吴经壶属紫砂肇始之器,当无疑问。吴经壶不晚于嘉靖十二年,金沙古井壶虽然在形态上比吴经壶更为原始,但时代却可能略晚于吴经壶。原因就是宜兴紫砂器创始之初便产生了两个发展方向(图一)。一种是民间实用之器,如金沙古井出土之物。器形粗旷且不加修饰,另一类如吴经壶般,点滴中透着文人雅客的奇思妙想。张渚1509年就记述了煮水沦茶的详细过程,注汤用的是壶,煮水用的虽未明说,大体应该是瓷或锡铫。再看吴经壶,鼓腹小平底,和王问所画之壶无异。当为煮水之用。虽名为壶,实用作铫也。嘉靖十三年成画的文征明《品茶图》中,炉火之上的煮水器从横把造型看应为紫砂穿心铫无疑。那么至少嘉靖中期文人已经开始使用紫砂穿心铫,而紫砂壶的功能已经转化为单纯的注汤器了。目前所见最早的紫砂穿心铫是近年徐州卫遗址出土的,时代不晚于天启四年。至时大彬时代,紫砂壶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新阶段。文人墨客争相追逐大家茗壶,紫砂壶的造型变化增多,壶上刻款开始流行,漳浦壶及扬州壶即为此期代表。及至时大彬“后游娄东,闻眉公与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紫砂壶更趋于文人雅玩了。华师伊壶当具此期特征。金沙古井出土的壶和罐代表着紫砂器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高领口平底罐共的底部和腹部多烟炱黑灰,应为煮水之铫;而出土的壶已经作泡茶之用了。这种高领口罐煮水、提梁紫砂壶注汤的使用方式在民间一直沿用,并无变化。在蜀山窑址明代地层中的同类器物证明了这一点。直到清代初期,民间才开始使用紫砂穿心铫。
现在“紫砂穿心铫”的泛起不仅填补了紫砂工艺史中吴径提梁壶到时大彬之间的一段空缺,而且为研究明代文士茶道及紫砂工艺发展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而出土该砂器的窑址的发现也增补了历史上明代早期紫砂窑址的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