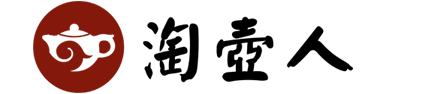凡事总会有个标准、有个法度,以此作为相互比较的基础,便可轻易分出高下,文物鉴赏亦然。文物鉴赏有个方便的法门,即是“标准器”,有人说“一部陶瓷史几乎可以说是由一连串标准器组成的。”的确,我们可以较轻易地利用已知的标准器(例如窑址标本、纪年墓出土器或器物本身带有可信年款的陶瓷器),通过“比较法”来作出具体的对比。目前看来,可供作紫砂标准器者,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
(一)墓葬出土器
历来墓葬出土物便是文物考古最可靠的标准器。但遗憾的是,宜兴紫砂由于年代不过五百年,明清墓葬对考古界而言,发掘的必要性较低,而往上的宋代墓葬,至今发掘已不下数干座,却没有在任何宋墓中出土过一件紫砂壶!因此,通过严谨可靠的考古发掘而出的紫砂标准器确实十分有限,目前较可供参考的是2004年年底,在南京博物院艺术馆展出的((砂壶汇赏——全国出土紫砂茗壶、南京博物院藏紫砂茗壶、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藏紫砂茗壶展》。该展展出了全国各地的出土紫砂壶,有江苏、福建、浙江、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7个省份14个文博单位收藏的明清时期29把出土紫砂茶壶,将这么多地区、这么多数量的出土紫砂茗壶集中展示,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次展品出版有《砂壶汇赏》大型图册,未能现场亲睹者,不妨找来看看。

吴经提梁
(二)古窑址残器
除了墓葬出土物外,古窑址残器也是另一可靠度甚高的标准器,但值得注意的是,古窑址残器的年代解读应充分尊重专家学者的共识形成,以下兹举一例: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古窑址,此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在其废品堆中发现了大量早期紫砂器废品,以各式壶类为主,有大量的壶身、壶嘴、提梁、把手和器盖出土。有学者依其堆积层分布,发现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代南方流行的龙虎瓶风格一致,并有宋代小砖一起出土,推断其“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早期。”并命名为“羊角山古紫砂窑”。学者冯先铭、贺盘发、杨振亚、刘汝醴、吴山及陶人顾景舟乃据此支持宜兴紫砂起源于宋代。但此说并未能形成共识,近年来多有考古学者撰文反驳,举证认为紫砂陶器起源于宋代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由于事关宜兴紫砂起源年代,各界都认为应早日着手寻找更可靠的证据,终于在2005年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无锡市博物馆、宜兴市文管委和宜兴市陶瓷博物馆组成的宜兴市古窑址联合考古队,对宜兴市丁蜀镇蜀山古窑址进行试发掘,共发掘面积334平方米,出土各类陶、瓷标本万余件。堆积层次厚达11米,断代标尺基本确立;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在此发现了明代晚期的堆积,估计也是一处古窑址;同时还发掘了一个清代中期停烧的古窑址。考古人员并在各堆积层发现了大量从明末清初到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紫砂残片。考古队领队杭涛表示:“从这次考古发掘来看,可以初步断定紫砂被有目的地使用,应始于明中晚期。”此次考古调查可望解决目前颇有争议的紫砂起源问题。

清中期御制描金朱泥诗文山水六方莲子壶
(三)水下考古发现
近年水下考古研究方面迭有所获,研究所得的结论更成为文物考古、断代的重要佐证,其中南洋水下考古的成果尤其受到学界重视,并被赋予较高期待。南洋也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咽喉和国际贸易、货物转运、集散的重镇。当然,这条海上丝路之路下所蕴藏历代沉没商船中的大量文物,也成为今日研究贸易史、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的重要宝库,更是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在南洋陆续出水的陶瓷器中,不乏有宜兴紫砂陶器,如乾隆十六年十二月(1752年1月)在南洋沉没的捷达麦森号(Gelder—malson)(又称南京号);再如道光元年十二月(1822年1月)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Tek Sing);又如道光年间(1845年前后)在南洋沉没的迪沙如号(Desaru)。这三艘沉船所发现的宜兴紫砂陶器各具特色,也传递出若干可贵的文史信息,值得注意参考。

龚心钊旧藏陈仲美兽钮紫砂壶
(四)文博单位典藏品
国内外各文博单位多半典藏有数量不一的紫砂壶,其丰富性与保存状况也较前述三种标准器能提供更为完整具体的信息,尤其是该博物馆若有可靠的入藏年份、来源那就更具参考价值,例如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在1949年以前的那批清宫旧藏紫砂器,就在断代上提供了较可靠的参考。再如欧洲德累斯登博物馆(Dresden Muse—um)在康熙六十年(1721)入藏造册的120件宜兴紫砂器,也具备同样的参考价值。顺便提一下一个有趣的实例:南京博物院藏陈鸣远款“笋形水盂”,1982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美乃美会社合作出版的《中国陶瓷——宜兴紫砂》,将其断为“明” (陈鸣远应为清初陶人),今日一般共识则为“清代”。但顾景舟在前南京。博物院梁白全院长主编《宜兴紫砂》时,表明此器为早年所仿制,该书乃据此而将其断为“近代”。令人迷惑的是,次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顾景舟主编的《宜兴紫砂珍赏》中。顾老的出尔反尔的确令人困惑不已。笔者试着寻找相关片断史料,推测当年顾老欲言又止的心态:很可能顾老当年在上海仿古时期的确制作过此式的“笋形水盂”,(其实至少蒋彦亭、范正根也都仿制过以笋为题材的水盂文玩,所以在1997年《紫泥清韵——陈鸣远陶艺研究》一书中,可看到七八件大同小异的笋形水盂)或许因时隔半个多世纪,顾老已难分辨何者是自己当年手泽了。事实上,经过南京博物院曹者祉查证,这件陈鸣远款“笋形水盂”是在1958年由上海何天麟所捐赠。而此器又是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1895~1934)赠送给何天麟父亲的。吉鸿昌是察绥抗日同盟军兼北路前敌总指挥,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被捕,24日在北平就义。所以吉鸿昌赠送笋盂最迟当在1934年秋天,而事实上应该更早。但顾老当时尚未及弱冠,正在家中由其父聘来的储铭传艺两年中(1934~1935),亦即尚未应郎玉书之聘到沪上仿古,因此在时间上显然有误。

值得注意的是,文博单位的典藏品也并非件件都可作为标准器,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新人藏的紫砂壶更应谨慎以对,主要的理由是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有过一波高水平的仿古潮,在这个权贵征逐的十里洋场中,字画瓷器无所不仿,紫砂古陶器更是备受市场欢迎的收藏品类,需求度甚高。嗅到商机的古董商如郎玉书、虞顺恩、汤邻石,陆续招兵买马,秘密投入仿古事业。另有收藏家如龚心钊、莫悟奇等人。他们分别自宜兴聘请了裴石民、蒋彦亭、王寅春、顾景舟、蒋蓉等制陶高手到上海工作,并提供特制的泥料、仿古的图样、特制的辅助工具(如筋纹模具、印纹模板),当然还有傲视宜兴同侪的薪资。为求最佳效果,商人们不惜成本地从宜兴买土、配土,运到上海制坯,然后钤刻明清各紫砂名家的款识,运回宜兴烧制,并经作旧处理后,由专人运回上海,以真古董出售。由于这些陶工都是一时之选,而且制造这些精品的时间并无限制,三月或五月不等,务求精益求精。因此,陶工们所创作的精品,质量远胜于他们供应宜兴和上海各陶瓷公司的素坯。这些仿品均源于名家旧器实物,且水平极高,遗存至今为鉴别工作带来相当的挑战,今日部分文博单位典藏品中就有若干是这些早期精致的仿品(多是征集或捐赠入藏的)。为此宋伯胤先生尝言:“我认为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才能摆正这个历史阶段的紫砂陶人在中国紫砂陶史上的地位。因此,我认为当前紫砂陶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三十年代的作者作品及其有关文献数据的征集研究上。”

(五)文献著录
明清、民国的紫砂文献,如《阳羡茗壶系》、《阳羡名陶录》、《茗壶图录》、《阳羡砂壶图考》当中著录的数据有些是可以当做参考的,例如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时大彬“或淘土,或杂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又“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竞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次则李仲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已。仲芳亦时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逊。”再如吴骞《阳羡名陶录》说陈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予尝得鸣远天鸡壶一,细砂作,紫棠色,上锓庚子山诗,为曹廉让先生手书,制作精雅,真可与三代古器并列。窃谓就使与大彬诸子周旋,恐未甘退就邾莒之列耳。”这些工艺特色的描述因与作者年代相去不远,因此都是较为可信的。但如果是像《阳羡砂壶图考》所载的“碧山壶馆藏猪肝色大壶,泥质湿润,工巧敦朴兼而有之,底镌行书‘叶硬经霜绿,花肥映日红,大彬制…、“张叔未得时少山方壶,底锓‘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二句,欧公诗也”,或陈鳇《松砚斋随笔》:“客耕武原,见茗壶一柄于仉氏六十四砚斋底有铭日‘一杯清茗,可沁诗脾,大彬’凡十字”,又或者是见到与奥兰田《茗壶图录》中线描壶形、款识一样的便要小心了,因为姑且不论前人所述的真伪如何,但在今日已有太多的伪作是按照文献著录的特征去制作的,且其用泥、造工皆循古法,依样重制、作旧,再编个离奇动人的故事,爱壶人若稍稍“按图索骥”、“见猎心喜”,极易坠入壳中。古人早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应谨记在心。
总而言之,以上每类的标准器都能提供不同程度的解读信息,对于鉴赏工作的帮助虽非全面,但也能反映出那个时空的若干蛛丝马迹,虽然有限,却也弥足珍贵了。

顾景舟此乐提梁壶